|
全民K歌充值 触摸莫洛陈光建 偶然在地图上找到莫洛,放大以后,能看清的也只是峡谷深处隐约的几栋彩钢瓦覆顶的房屋。从米林县里龙桥拐进里龙沟,沿着里龙河(地图上标注为里龙普曲)一直走,可以到达莫洛。记得当年走这条路时,有人说从里龙到莫洛有一百多华里。按照地图上的比例尺,直线距离仅有四十华里,现实中的路,是隐在原始森林中的弯曲小路,所以,只看地图作战是会误事的。每一次看这条蜿蜒细小的图标路,都像是在寻找一个遥远的梦境,这个梦境早已隐没在那片莽莽苍苍的原始密林中。 莫洛,是位于西藏米林县喜马拉雅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,那里有边防团的前沿哨所。翻过哨所前面的山脊,就是伪阿鲁纳恰尔邦。当年,英国殖民者用五千条淘汰的破枪诱使噶厦政府接受了非法的“麦克马洪线”,由此,藏南的大片国土划归他人版图,至今不能收回。 将人生看作过客,似乎太过宿命。我在十八岁那年冬日的某一天到过莫洛,严格说只在莫洛的村旁停留了一个小时,譬之触摸,应该是恰当的。而莫洛给我留下的印象,却终生难忘。 一九七一年底,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,驻扎在西藏边防的部队一直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。记得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初的一天,全团在卧龙台集合,团长作了冬季拉练动员,这次拉练动员更像是一次战前动员。回到连队后,连长又作了详细的说明,从连长的话语中,我们感觉这可能是一次实战。一听说要打仗,我们这些入伍一年的新兵兴奋莫名,个个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,每一个人都写了请战书。争取入团、入党的,在请战书里都写了相同的一句话“请党组织在战斗中考验自己”。在留下的包袱上写完自己的家庭地址,和父母亲的名字(如果‘光荣’了,这些东西会作为遗物寄回家中),我并没有感到恐惧,而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激动。三十三团在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立下过战功,十年以后的这次行动,三十三团又作了先锋。 拉练动员后的第三天,特务连先行,提前一天出发。考虑到行军路线要经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,连长将工兵排安排在最前面,如遇倒伏的大树挡住去路,即由工兵排除障碍。我是工兵一班的战士,自然走在前面。因为是冬季,冬装不算,皮衣或被子,毛毡,雨衣,武器,加上七天的主副食,每个人负重都在六十斤以上。负重行军是高原战士的必修课,背着五、六十斤重的行装,每小时走十多华里,绝对是对意志力的考验。刚下卧龙台,连队士气高昂,歌声不断。转过一个山嘴后,歌声渐稀。各排之间拉起了口号,工兵排喊“苦不苦,想想红军二万五!”,侦察排和警卫排回应“累不累,想想革命老前辈!”一路上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!”的语录歌声,口号声此起彼伏,震天动地。抵达里龙桥时,已是下午两点。部队在桥头河滩上以班为单位起灶做饭,稍事休息。大约五点,工兵排走进里龙沟。 沟口河水湍急,清澈见底,河岸边生长着野生灌木,其中沙棘居多。一进沟,迎面就是松林,入冬后,红松的针叶已经变成红棕色,杉树依然青翠,近景是沙棘树上一簇簇橙黄色的果子,加上蓝天白云衬托,远远望去,宛如一幅天然油画,我们就行走在这幅画中。小路在林间蜿蜒,不时从密林深处传来窸窸窣窣的,类似伐木的声响,那是啄木鸟啄木的声音。不知名的鸟在附近鸣叫,鸣声在林中悠扬悦耳。忽而有猕猴的啼啸,凄厉悠长。经过六、七个小时的行军,队伍已经安静下来,这群年龄在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,默默地往前行进。 傍晚七点,天色暗下来,我们在一片林间开阔地宿营。里龙河在不远处奔流,哗哗有声。两边山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,开阔地杂草丛生,高可没人。这里原来曾是一个村落,毁于地震,留下几处房屋倒塌后的残垣断壁。我们班找了一堵残墙背风处,两人一组用雨布搭起帐篷,一床毛毡垫在地上就是床,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和皮大衣,高原十二月的夜晚,气温很低,野外露营,为防止感冒,棉军帽不能摘下,袜子也不能脱,好在抱团取暖,年轻气盛,加上一天行军的疲劳,大家很快就进入梦乡。半夜轮到我站哨,钻出被窝的那一刻,内心纠结,但当我抬头看到满天星斗时,一切都复归平静,高原冬夜的星空,没有词语能描述它的美。斗转星移,一个小时转瞬即逝,钻进被窝后,我还在想那些在湛蓝天幕上倏然划过的流星,那样匆忙,它们究竟去了哪里?如果一颗流星代表一个逝去的生命,我的那颗又在什么地方?隐约记得那晚的梦里有璀璨的银河,和无数的流星。早上六点半,天还没有亮,朦胧的晨雾中,我们收拾完行装,在河边挖灶做饭,饭后稍事休整,沿着林间小路继续行军。 今天,有人将这里称为人类最后的秘境,当年走在这秘境里的年轻战士,年龄最小的,也已经年过六十七岁了。谷歌卫星地图上,里龙普曲流经的山谷,满眼青绿,仍然保留了原始的状态,那些几百年,甚至上千年的大树,就隐在青绿之中。当年,我们在这青绿里行走。小路转弯处,崖壁上有雕刻的佛像,我看佛像时,佛像也在静静地看着我们从他面前经过,是不是像昨夜我看流星,一晃而过?欲问佛像,而眼前的佛像仍是一脸安详,神秘。一行人在林间小路上行走,空气是极端的新鲜纯净,可是背负的行装却越来越沉,你能听到的,除了密林里鸟兽的鸣叫,就是战友和自己急促的呼吸声。事隔久远,中午在哪儿吃的饭已记不清了,填充记忆的,只有原始森林里浓密的绿色,那绿使人的心境平和安静。傍晚,我们在离莫洛大约还有四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宿营。两天行军后,大多数人脚底都打起了血泡,经卫生员处理后,一行人早早就睡了。 第二天早上,我被咕咕的鸣叫声吵醒,起来看时,相隔十米的小河对岸有一群藏马鸡在林间觅食,看见有人,却没有丝毫的惊恐,这里本来就是它们的家园。早饭后,打好背包,队伍继续前行。十一时,我们到达莫洛,远远能看见村里的房屋和炊烟,以及边防连的岗哨。排长命令就地待命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边起灶做饭。饭刚收水,小路上传来嘚嘚的马蹄声,通信连的战士下马递给排长一纸通知,团部命令先头部队紧急后撤,在夜里十点以前到达里龙桥。排长一看手表,已经过十二点了,也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十个小时,却要赶一百多里路。来不及看莫洛的景色,我们将一锅将熟的米饭留给村里出来的妇女和小孩后,转身就走。 回撤的行军速度很快,三个小时后,一些年龄小,身体较弱的战士开始掉队,有人因为身体不适,血泡未消,背负沉重,与前面战友的距离越拉越大。排长命令三位副班长和体力好的战士断后收容,前面的人能走多快就走多快,务必在夜间十点前赶到里龙桥向团部报到。那年我十八岁,幸运的是脚底只有一个小泡,昨晚引流后已不再碍事。看到有战友掉队,一咬牙将他的枪拿过来,连同自己的,两支步枪,共有十多斤重。时隔多年,已想不起那段路是怎样走过来的,只记得我是最先到达里龙桥的那几人之一,连长看表,差十几分钟到十点。放下背包,棉罩衣背后浸出的汗水结成了一片盐渍。我的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,倒在地上就不想起来了。后来才知道,我们这次去莫洛,是为准备牵制印军的大部队开路,事因外交策略,才导致了这次紧急后撤。 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上,有战友说在那次后撤的路上,如果不是因为我鼓励他,帮他扛枪,留下压缩饼干,他可能不会坚持走出里龙沟。因为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,人会悲观沮丧,在黑夜笼罩的原始森林中,人会产生幻觉,那年他十七岁。对于这件事,我已经印象模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们为什么还如此怀念西藏,怀念在特务连的日子,怀念莫洛之行?我想,人在经历生理和心理的极限考验时,犹如背水一战,能够迸发出压倒困难的胆量;更像精钢淬火,锻造了自身的坚韧。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,共同的经历结成的战友之情,必定令人终生难忘。 今年,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胜利六十周年,我们纪念六十年前那场保卫祖国西南边境战斗的胜利,更加怀念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,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。地图上,莫洛往下,“麦克马洪线”以南,那一大片绿色,原本是祖国的领土。作为中国人,永远都不能忘记。 (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) 作者简介: 陈光建:四川成都人,祖籍安徽嘉山。1971年入伍,1976年退伍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直属特务连文书兼军械员。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《清远堂遗笺》一书作者,《印鉴-易均室辑拓印谱两种》特邀编委。《成都文物》,《文化成都》自由撰稿人。 作者:陈光建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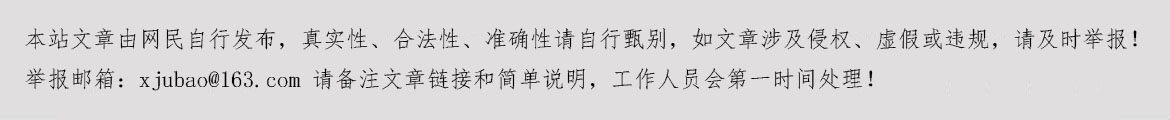
|
|
1
 鲜花 |
1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
业界动态|塞纳网

2025-09-18

2025-09-18

2025-09-18

2025-09-18

2025-09-18

请发表评论